名人名家與元宵節之宋元夕風月談
來源:廈門小魚網 發布時間:2021-02-04 15:17:23
“紅杏尚書”宋祁的“艷遇”
北宋仁宗年間,正值趙宋王朝的承平盛世,正月十五上元佳節是都城汴京一年之中最熱鬧的夜晚。十里春風裹華燈的美景,吸引著如織游人,也吸引了素好聲色繁華的龍圖閣學士宋祁。這位因“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之麗句而得名“紅杏尚書”的才子那幾年正和同僚歐陽修一起奉命修撰《唐史》。雖然公務繁忙,但少年登科、官運亨通的經歷讓宋祁仍保有一種倜儻瀟灑的詩人做派。同在朝中任高官的哥哥宋庠曾提醒他勿要耽于享樂,常思昔年寒窗淡飯之苦。宋祁卻不以為然地回敬乃兄,十年寒窗苦讀,不就是為了今日嗎?
宋祁的驕傲是有原因的,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他和哥哥同科應考,雙雙高中,宋氏兄弟首擢雙魁的美談一時膾炙京中,仁宗皇帝還特地下令在他們的家鄉雍丘修建雙塔,以示表彰。隨著兄弟倆步入官場,交游漸廣,“大宋”、“小宋”的稱呼也在朝中流傳開來。“大宋”宋庠為人清約莊重,日后官至宰相,是受人敬仰的端方君子。“小宋”宋祁則才子氣十足,不但文采出眾、博學敢言,生活上也頗有情趣,家中多蓄婢妾聲妓,宴飲時手賦新詞,即命佳人當場彈唱,再經由好事的賓客一傳,宋祁的即興之作往往成為風靡京城樂坊酒肆的流行小曲兒。
漫步于上元之夜熙攘的繁臺街,眼前的奇燈妙舞和賞燈仕女們的窈窕倩影又引發了宋祁的詩興。忽而一陣人馬喧囂打斷了他的思緒,只見翠華遙遙,久居內苑的皇家宮娥們也在這一天被特許出宮觀燈,與民同樂。宋祁正準備為皇家車隊讓路,只見迎面而來的一輛寶馬雕車忽然掀起半角繡簾,燈影煌煌中,一張施著宮妝的如花嬌面向自己微微一粲,輕喚道:“小宋。”車隊隨即遠去,彼姝音容如夢如幻,宋祁驚訝之余感慨萬端,當即吟出一闕輕柔儇巧的《鷓鴣天》,記載這番元夕之夜的神奇“艷遇”:
畫轂雕鞍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金作屋,玉為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
在這首詞中,宋祁兩次引用了唐代詩人李商隱的名句,抒寫茫茫人海中與那位不知名的宮娥擦肩交目時的心心相印和旋即香塵遠去的悵然若失。“劉郎”借用東漢劉晨、阮肇入山采藥偶遇仙女留宿、后欲再尋卻迷途不可至的典故。暗指彼此因身份地位之隔而不可氣息相通的憾恨——畢竟對方是“金屋玉籠”中的貴眷,就算風流如宋祁,身為人臣亦不敢多想,只好將這一腔癡意化入詞中,自抒綺懷。
或許是這份可望而不可得的美麗情愫引起了大家的共鳴,元夕幾天的燈市還未結束,宋祁這首《鷓鴣天》已流傳在滿城歌兒舞女的鶯喉之中,乃至一直傳唱到禁城內,宋仁宗也知曉了這番“桃色新聞”。性情寬和溫厚的仁宗皇帝遂問當晚叫小宋的是何人,那位宮娥便站出來說:“頃侍御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曰小宋也,時在車子偶見之,呼一聲爾。”她因為前不久某次侍宴時見過宋祁,上元燈夜于街中邂逅,情不自禁就喚了一聲,不想卻引出一段風月詩緣。仁宗于是召見宋祁,談及此事,不慎捋到龍須的宋祁惶恐萬分,仁宗卻引其詞意笑侃道“蓬山不遠”,將那位宮娥賜給了宋祁。
這段故事見于南宋著名學者黃升編著的《花庵詞選》,是附錄在才子詞人們作品之后的趣話逸聞。其實,縱然未得天子一笑點鴛鴦,宋祁這首詞中所刻畫的“卿須憐我我憐卿”、“一見知君即斷腸”的相知相惜之意,也足以在千載之下感動讀者。
深情詞客姜夔的月下癡吟
有情人成眷屬是說書人的善意,而不知所終的衣香、柳暗花明的凝望,從某種意義上更符合文人騷客筆下元夕春宵花月夜的美學情調,為愛情的升華留下了浪漫的想象空間——并不是每一位宋代才子的元夕情事都能以甜蜜收場。生活在南宋中期的詞人姜夔,就和深愛多年的女子在元宵節前后分手,承受月圓人散的失戀之苦,并為此悵惘了一生。直到年屆不惑、兒女雙全之時,深情的姜夔仍會被元夕佳節的燈火勾起心中刺痛,寫下多篇纏綿悱惻的懺情小令,在宋代元夕詞中點染出一抹獨特的凄艷之色。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在文學、音樂和書法方面都稟絕世之才,更兼品貌秀雅、性情孤潔,被時人贊嘆有魏晉高士之風。然而,清才和浮名并沒有為姜夔帶來多少實質的幸福,少年貧病失怙,青年屢試不第,他一生中的大多數年頭,都是攜琴簫書畫漂泊于江淮之間,居無定所,四處寄食。好在當時偏安江南的士大夫群體中流行一股風雅的養客之氣,“南宋四大家”中仕途顯貴的楊萬里和范成大,都賞識姜夔的詩文辭采,將他聘為門客,詩壇前輩蕭德藻更是招其為侄女婿。
以一布衣之身抱得名門千金,以當今的世俗眼光看來可謂齊人之福,但在姜夔此時及之后的詞作中,并不見愛情美滿的喜悅,卻一再流露出對少年時代某段悲戀的懷念,這便是姜夔詞集中著名的一個主題——“合肥情事”。據民國詞學宗師夏承燾考證,姜夔二十出頭時客居合肥,愛好音律的他在勾欄中結識一位解語善奏的妙齡歌姬,彼此引為知音,相戀數年。但戰亂和生計迫使姜夔輾轉他鄉,與愛人幾番離合,最終天各一方。兩人最后一次分別正值上元時節,在滿城春柳和紅蓮燈籠之下,姜夔離開了鐘情十余載的女子,此后他一生再也沒有機會重臨合肥,亦再也無法如常人般在歡聲笑語中度過歲歲元夕。
多年之后,姜夔曳裾于都城臨安的豪客之門。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的元宵節,臨安城沿襲著北宋時期提前放燈的習俗,才到正月十一,西子湖畔已是花燈如晝。姜夔肩上馱著粉團團的小女兒,擠在嬉樂的人群中,想去尋覓一些蒼茫人生中的瑣碎歡愉。在其詞作《鷓鴣天·正月十一日觀燈》中,記載了當晚的見聞與心緒:
巷陌風光縱賞時,籠紗未出馬先嘶。白頭居士無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隨。 花滿市,月侵衣,少年情事老來悲。沙河塘上春寒淺,看了游人緩緩歸。
眼前回光返照般的極致聲色,讓姜夔懷念起過往生命中美麗易逝的瞬間,悲從中來,游興陡失,悄然退出了儷影成雙的歡游隊伍。到了正月十五當晚,他害怕觸景傷情,早早閉門高臥,卻難以成眠,只好“芙蓉影暗三更后,臥聽鄰娃笑語歸”。此時,距離他與合肥歌女初識已過去二十年,那段刻骨銘心的往事化成了元夕夜的一宵春夢,夢醒愁思愈濃,姜夔用與之前同樣的詞牌慨然長嘆:
肥水東流無盡期,當初不合種相思。夢中未比丹青見,暗里忽驚山鳥啼。 春未綠,鬢先絲,人間別久不成悲。誰教歲歲紅蓮夜,兩處沉吟各自知。
在這首副題為“元夕有所夢”的詞中,姜夔用絕唱般的深情追思淮南皓月下的舊愛。雖然今生情緣已如夢幻泡影,但他堅信二人曾經的感情真摯皎潔如元夕滿月,對方一定也會在年年今夜因嗟嘆往事而沉吟不眠。初分別時的痛苦心潮,如今已被時間磨損,說是“別久不成悲”,其實悲哀化為了更加深沉彌遠的憾恨,與紅蓮燈的雋永意象一起牢固地埋在詞人的心頭。
躲過了正月十五,情難自禁的姜夔又忍不住出門去賞燈散心。并寫下最后一首詞,副題為“十六夜又出”:
輦路珠簾兩行垂,千枝銀燭舞僛僛。東風歷歷紅樓下,誰識三生杜牧之。 歡正好,夜何其。明朝春過小桃枝。鼓聲漸遠游人散,惆悵歸來有月知。
如舊的東風,如舊的佳節,歡游往事歷歷,卻像已隔三生。唐代詩人杜牧亦曾因機緣變幻錯過意中女子,留下“狂風吹盡深紅色,綠葉成蔭子滿枝”的悵嘆。姜夔以此自喻,感嘆風流易逝,空留悔恨,一捻余情唯有今宵孤月憐知。杜牧尚有遍贈珠簾的艷名,姜夔一生作品中不停懷念的卻只是這一段情。明朝新春將至,又是桃花盛放時,但看花者春心已死,人間一切繁華美麗已與他無關。
就在寫下這組元夕悲戀詞作的前后,姜夔在事業上也受到了一番打擊。這一年,他有感于國家南渡后禮樂不全,典籍散佚,遂撰《大樂議》、《琴瑟考古圖》等上書朝廷,但沒有得到重視。后來,姜夔再次獻上《圣宋鐃歌鼓吹十二章》,終于獲得禮部的青眼,并被破格“免解”,也就是不用經過解元的鄉試,可直接參加由禮部舉行的省試。但他依然在應舉時落選,從此完全絕了仕途之念,以布衣之身落拓終老,也讓姜夔養成“野云孤飛,去留無跡”的清空詞風。而那幾首元夕詞,卻格外蕩氣回腸,記錄著這位薄命才子郁郁多年的不悔深情。
以“情”抗“理”的宋代元夕
縱觀兩宋三百年的詞壇,名家們在元夕夜題詠和感嘆愛情的作品不勝枚舉。歐陽修憧憬“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的佳境,柳永捕捉到“香徑里,絕纓擲果無數”的幽歡,辛棄疾為“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驚艷瞬間擊節而嘆,孀居的李清照自認中年多難的自己無有那些有著生命熱情和歡愛渴望的少男少女的逸興,只好“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這些著名辭章中閃爍出的華美情思,與人們印象中宋代理學盛行、禮法森嚴的生活氛圍似乎有所出入,難道那時的才子佳人真可以在月下自由相約、擲果定情?
這與當時的社會心態以及元夕獨特的民俗有關。在宋代,城市經濟空前繁榮,富足的生活滋養了人們性情中的浪漫一面,使宋代的市民階層有精神余力去追求世俗之樂。宋代筆記小說中多見對城市生活與享樂之風的記載,“游湖”、“納涼”、“開爐”、“賞雪”等休閑趣目穿插于頻繁的節慶中,豐富著人們的社交場景和情感體驗。宋人所追求的現世幸福,自然也包括美滿婚姻與真摯愛情。在宋詞創作中,正是以相思歡愛為主題的作品數量最多而成就最高,它們的作者從公卿到庶民,折射著普遍存于宋人意識中的肯定真我、渴望真情的心態。華燈達旦不設宵禁的元夕佳節,正是這種心態集中釋放的出口。
元夕行樂的習俗興于隋代,自唐玄宗開元時起因“放燈三夜”而歡鬧升溫。至宋時,因“朝廷無事,區宇咸寧,況年谷之屢豐,宜士民之縱樂”,宋太祖下令將元宵節又增設兩夜,由朝廷主持都城汴京的燈會與慶典,鼓勵男女老少、官民僧俗皆來玩賞。這種全民狂歡的情調使得宋人對于元夕有著別樣的期盼,特別是對于久居深閨的女子們而言。正如《牡丹亭》中杜麗娘游園時春心萌動,璀璨的花燈和歡騰的氣氛為女兒家帶來一種心照不宣的誘惑,她們在這晚盛妝出行,頭戴蛾兒雪柳,足踩俗稱“錯到底”的時尚鳳頭鞋,讓自己成為燈火之中的一道麗景,也牽動著四周翩翩少年的目光。南宋詞人劉辰翁一語道破了宋代男士們元夕之夜的心態:“不是重看燈,重看河邊女。”
元夕弛禁為原本授受不親的世俗男女創造了自由接觸的空間,浪漫的燈夜更是營造出一見鐘情的如夢佳氛。嬉笑冶游之際,禮法禁律退居其次,從眉目傳情到私換信物,宋代城市青年男女們將平日壓抑的內在熱情于元夕狂歡夜大膽釋放。
他們明知此舉不容于倫常家規,五夜燈節一過,宵禁重啟,那森嚴的禮教又將凌駕于情感之上,扼殺這番未經媒聘的戀愛。游戲感情的人會把元夕艷遇當作人生旅途中一個甜蜜片段,但對于癡情者而言,為了這一份人月雙圓的相知相戀,或許要付出多年乃至一生的等待與尋盼,這就使得情人私奔成為宋代元夕之夜的常見行為。
宋人羅燁筆記小說《醉翁談錄》中記載了一對青年男女私奔的故事:元夕夜,張生路過慈孝寺殿前,拾得一方裹著香囊的紅綃手帕,上有女子筆跡寫著“有情者得此物,如不相忘,愿與妾面,來年上元夜請于某處相待,車前有雙鴛鴦燈者是也”。
第二年元夕夜,張生如約而至,“認得雙鴦燈,果得之”,與帕子的主人、某太尉家中偏室李娘成功會面。二人互訴衷腸,并于次夜私奔出城,開始了新的生活。在宋代,有不少像李娘這樣對婚姻不滿的女子趁元夕夜出游另覓佳偶,雖然并非人人都能如愿收獲美滿新緣,但她們勇敢追求愛情的行為沖擊著封閉的社會心理,為文人墨客所感所傳,從而啟蒙了更多青年男女以“情”抗“理”,光彩灼灼地彰顯出內在生命的本真。從這個意義上,沉淀下無數溫馨花絮的宋代元夕無愧于“情人節”之名。人生有限,王朝有終,那承載著一段段不了真情的宋代元夕詞,卻穿越時空感動后人,成為人們文化心靈史的一部分。
相關話題
- ·名人名家與元宵節之宋元夕風月談2021-0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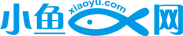
 閩公網安備35020302000108號
閩公網安備35020302000108號
